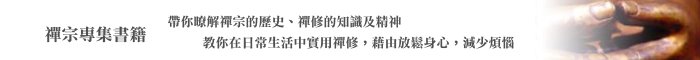第四節明末的唯識思想
溯源:要瞭解明末的唯識思想,應先瞭解《華嚴經疏鈔》及《宗鏡錄》兩部書的中心思想,以及元人雲峯的《唯識開蒙問答》究係說了什麼?
《華嚴經疏鈔玄談》卷二說:「相是即性之相,故行布不礙圓融;性是即相之性,故圓融不礙行布。」(註一)卷三又說:「如如來藏,雖作眾生,不失佛性故。(《華嚴經》)〈出現品〉云:佛智潛入眾生心。」又云:「眾生心中有佛成等正覺。」(註二)雖然明知唯識學中,以八識為生滅及涅槃之因,法爾種子,有無不同,故說五性差別,既立識唯惑所生,故立真如常恆不變,不許隨緣。也知《楞伽經》及《大乘起信論》等的主張,與唯識家不同,以為八識通於如來藏,隨緣成立,生滅與不生滅,和合而成,非一非異,一切眾生,平等一性,所以真如隨緣。這是性相二宗的矛盾處,可是依照華嚴宗教判立場,建立五教差別,唯識是僅高於小乘,而稱為大乘始教,性宗是第三,稱為大乘終教,到了第四,大乘頓教如《維摩經》等經,即已不說法相,唯辨真性,訶教勸離,毀相泯心。而此四教,均非究竟,到了第五大乘圓教,即是華嚴宗的立場,則唯是無盡法界,性海圓融,緣起無礙(註三)。故說法相法性,無不從此法界流,無不還歸此法界。真心與妄心,八識與真如,隨緣不隨緣,根本原是同一法界體性,合則互成,分則雙乖。
《宗鏡錄》的楊傑序云:「諸佛真語,以心為宗,眾生信道,以宗為鑑,眾生界即諸佛界,因迷而為眾生,諸佛心是眾生心,因悟而成諸佛。」這是把真心、妄心合起來看的論調,亦即以圓教的立場,分析無差別中的有差別,有差別實即無差別。該序又說:「國初吳越永明智覺壽禪師,證最上乘,了第一義,洞究教典,深達禪宗,稟奉律儀,廣行利益,因讀《楞伽經》云『佛語心為宗』,乃製《宗鏡錄》。……所謂舉一心為宗,照萬法為鑑矣。」(註四)
《宗鏡錄》永明自序有云:「約根利鈍不同,於一真如(法)界中,開三乘五性。或見空而證果,或了緣而入真;或三祇熏鍊,漸具行門;或一念圓修,頓成佛道。斯則剋證有異,一性非殊。……唯一真心,達之名見道之人,昧之號生死之始。」又云:「物我遇智火之焰,融唯心之爐,名相臨慧日之光,釋一真之海。」又云:「遂使離心之境,文理俱虛,即識之塵,詮量有據,一心之海印,楷定圓宗,八識之智燈,照開邪闇。……但以根羸靡鑑,學寡難周,不知性相二門,是自心之體用。……如性窮相表,相達性源。須知體用相成,性相互顯。」這些,無非說明了永明的立場,是華嚴圓融觀而以一心統攝性相為主眼的。序中又說到他編《宗鏡錄》的用心及方式:「可謂搜抉玄根,磨礱理窟,剔禪宗之骨髓,標教網之紀綱。」又說:「今詳祖佛大意,經論正宗,削去繁文,唯搜要旨。假申問答,廣引證明。舉一心為宗,照萬法如鏡,編聯古製之深義,撮略寶藏之圓詮,同此顯揚,稱之曰錄。」(註五)
可見《宗鏡錄》乃是繼承華嚴宗的思想,主唱以一心為終始,以一心圓攝一切法,兼容禪教,融會性相。以一心為宗,統收一切經教,不論生死或涅槃,八識或四智、妄境與真如,均在唯一真心之內,所謂心、佛、眾生,三無差別,僅是為了眾生的根性有利有鈍,所以分別說出相和性。
《唯識開蒙問答》:此書共二卷,由「宣授懷益路義臺寺住持宗法圓明通濟大師雲峯集」,共計一百四十九題,以問答方式,介紹唯識,復以唯識為中心,介紹通常的佛教教義,乃至討論禪教一致、性相無別、三教同異等問題。既稱為「集」,表示係集前人著述而未申己見。但他所用資料,未必皆出於唯識系統,例如多次引用《楞嚴經》、《華嚴經疏鈔》、禪宗語錄,以及《維摩經》、《勝鬘經》等經。以是此書立場,雖在唯識,其體裁以及思想指導,似仍不出《宗鏡錄》的影響。
在上卷的「成唯識義」條下,有如下的問答:
「問:行其中道為極則否?答:未必。問:何以故?答:若執依圓,還同遍計。……問:如性宗云:二邊莫立,純中道不須安,同此義否?答:同。如禪宗云:有佛處不得住,無佛處急走過,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,似此義否?答:似。又云:恁麼也不得,不恁麼也不得,恁麼不恁麼總不明,此亦似否?答:亦似。」
「問:禪是禪心,教是佛語,焉得同也?答:佛心傳佛語,佛語說佛心,焉得不同。」(註六)
上卷的「能所成義」條下,又有如下的問答:
「問:成立唯識,有何義利?答:我佛法中,以心為宗,凡夫外道,背覺合應,馳流生死,菩薩改之,故造此論,成立唯識,令歸本源,解脫生死。」
「問:論者何義?答:教誡學徒,抉擇性相,激揚宗極。」(註七)
凡此,皆在表明《唯識開蒙問答》一書的思想背景,是因襲永明,溯源楞伽,以心為宗,敷衍法相而會法性。
明末兩流:明末的唯識諸家之中,大致可分二流:一是專攻唯識而不涉餘宗的,例如明昱及王肯堂二人,可為代表。另一是本係他宗的學者,兼涉唯識的研究者,則其他諸師皆是。雖然明昱及王肯堂,仍不能擺脫《宗鏡錄》及唯識的影響(註八),他們已盡量以唯識的立場,採用唯識系的經論,作為註釋的依據。從功力及內容而言,明末諸家的唯識著述,應以王肯堂的《成唯識論證義》,最為傑出,無論組織、說明、文辭,尤其是探索義理方面,極富於學術的研究價值。
唯識的唯識學:即是以唯識研究唯識的學者,他們未以圓融性相二宗為目標,只是希望把唯識學的勝義闡揚出來,為學佛修行者造福。唯識學主旨在以精闢的論理方法、謹嚴的組織分析,說明內在不動的識性以及外在變異的識相。菩薩即從識相而作重重分析,令眾生按圖索驥,轉識成智,泯相歸性。故說唯識,即是唯心。心有真妄,性有虛實,識有染淨。性宗如果一味重視圓修圓悟,易於形成不知心及心所污染程度,不識心性的真妄虛實,不別自身修證的確切層次,相宗則將心心所法的活動情況,心性的真妄虛實交代清楚,修證層次歷歷分明。若以《成唯識論俗詮》及《成唯識論證義》作比較,前者的依據較少,故偶有臆測之見。後者廣讀大小乘經論,雖亦有與窺基等之唐疏有出入之處,大致說來,已經盡了不違唯識之說的全力,乃是一部值得學者們細加研究的好書。
唯心的唯識學:即是以華嚴、天臺,或禪宗的立場,來研究唯識,雖然同樣竭盡心力,解明唯識的論書,也用唯識系的經論,作為解明唯識論書中的問題,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以唯識學作為他們某一層次上的橋樑或工具,此在明末的諸家中,又可分為四類:
以天臺宗為基礎的學者:紹覺廣承一系的諸人,皆以天臺為背景。例如大惠《成唯識論自考錄》自序有云:「(廣承)師三際敷揚,二時慈注,性相臺宗,一一傳習,尤慨臺相兩宗,久沒其傳。」(註九)因此,在他之後,至少有三位與天臺有關:
大惠於《成唯識論自考錄》卷一○,說明三身三土之處,即用天臺的四判教,謂:「橫論四教,豎則三土,同居四教,方便二教,實報一圓。」又引
《法華經.壽量品》句「大火所燒時,我此土安隱」,來說明《成唯識論》的「利他無漏淨穢佛土」(註一○)句。海幢居士廣顧的《成唯識論自考錄》後跋,亦說大惠「遍閱臺案」(註一一)。
大真的思想背景,於智旭的《靈峯宗論》卷八之一,說他學習其師廣承的教法,於慈恩、智顗、慧思的宗旨,每多遊刃有餘。
智旭不屬於天臺子孫,但他凡釋經論,均依天臺的方法,畢生主張教觀並重。例如《成唯識論觀心法要》的緣起文,劈頭便說:「夫萬法唯識,雖驅烏(沙彌)亦能言之,逮深究其旨歸,則耆宿尚多貿貿,此無他,依文解義,有教無觀故也。然觀心之心,實在於教外,試觀十卷(《成唯識論》)論文,何處不明心外無法,即心之法,是所觀境,了法唯心,非即能觀智乎?」(註一二)智旭曾作《教觀綱宗》,為後來天臺宗的入門書。《法華經》廣明本跡,故須立「觀心釋」一科,《成唯識論》直詮心法,成立唯識道理,即是觀心法門,所以他的註釋,名為《成唯識論觀心法要》。他的立場已極顯明。
以《楞嚴經》為基礎的學者:宋以後的性宗諸家,所依主要經論,大致不出《圓覺經》、《楞嚴經》二經及《大乘起信論》。明末諸唯識學者,除了明昱及王肯堂之外,無不引用此等性宗經論。而以通潤對於《楞嚴經》特具因緣,例如他在《楞嚴合轍》的自序中說:「予少孤,生於貧里。……爾時乃屬意《楞嚴》,且私淑王如會解。……丙戌,適無錫華藏啟《楞嚴》講期,主法者為先大師雪浪。……予始得看經法,自是以後,唯獨坐靜處,案上唯置《楞嚴》,即胸中、眼角、口吻邊,亦唯置《楞嚴》,且讀且思……積數年而《楞嚴》一貫之旨,字字皆契佛心。」(註一三)然在《成唯識論集解》之中,所引《楞嚴經》經文不多,倒是常見《大乘起信論》的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義、隨緣義、真如心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義等(註四)。
以《大乘起信論》為基礎的學者:凡是以性宗為立場的,無不重視《大乘起信論》,《大乘起信論》與唯識的觀點不同之處,主要在於《成唯識論》卷九的真如被八識依,既為生死依,亦為涅槃依,但其性淨不受薰,離雜染不隨緣,故待八識轉成四智,方與真如合一。至於《大乘起信論》的第八識,是生滅與不生滅的和合識,即是如來藏,又名真如隨染緣而入生死,隨淨緣則住涅槃,所以真如是可受薰的。研究唯識的人,當然都知道這點,但他們仍以圓融的觀點,將此兩流合而為一。此在明末諸師之中,可舉二例如下:
德清曾將唯識系的《百法明門論》、《八識規矩頌》,與《大乘起信論》相提並論。他在《八識規矩通說》的前言中說:「予不揣固陋,先取《起信》,會通《百法》,復據論義,以此方文勢,消歸於頌。」(註一五),又於《百法明門論論義》前言中,盛讚:「唯馬鳴大師作《起信論》,會相歸性,以顯一心迷悟差別。」又說:「其唯識所說十種真如,正是對(《大乘起信論》之)生滅所立之真如耳。是知相宗唯識,定要會歸一心為極。此唯《楞嚴》所說,一路涅槃門,乃二宗之究竟也。」(註一六)
智旭的思想,看似非常廣博,實則,其重心亦以《楞嚴經》及《大乘起信論》為依歸,尤其對於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推崇,甚至不惜批評了窺基,也指責了宗密(註一七)。在其所作《大乘起信論裂網疏》的自序中,先斥華嚴宗判《成唯識論》為立相始教,又判《中論》為破相始教,《大乘起信論》為終教兼頓之不當。又將《大乘起信論》與《成唯識論》的觀點連接起來而主張:「《唯識》謂真如不受薰者,譬如波動之時,濕性不動,所以破定一之執,初未嘗言別有凝然真如也。然則,《唯識》所謂真,故相無別,即《起信》一心真如門也;《唯識》所謂俗,故相有別,即《起信》一心生滅門也。」(註一八),又以《大乘起信論》與《大乘止觀法門》一書,在思想系統上,頗有淵源,所以智旭的天臺宗,每以南嶽慧思及天臺智顗並舉,毋寧說他是以《大乘起信論》與《大乘止觀法門》為中心的天臺學,故也是以《大乘起信論》與《大乘止觀法門》為中心的唯識學。
在《成唯識論觀心法要》之中,屢以《大乘起信論》與《大乘止觀法門》,作為論證或對比的說明。由此,便可瞭解智旭的思想背景了。
以禪修為基礎的唯識學:宋以後的中國佛教,不論僧俗,亦不論其以任何一宗的研修為專長,他們的出身,大概都與禪寺的禪僧有深厚的淵源。故也可說,明末的唯識學者,均有禪宗的背景,其中最突出的,是憨山大師,所以他的《百法明門論論義》,不為解釋法相,旨在便利參禪用工夫,現舉數例如次:
釋「作意」條下,他說:「故今參禪看話頭,堵截意識不行,便是不容作意耳。」
釋「五徧行」條下,他說:「其實五法圓滿,方成微細善惡,總為一念。……參禪只要斷此一念,若離此一念,即是真如心,故《起信》云,離念境界,唯證相應故。」
釋「行捨」條下,他說:「以有此捨,令心不沉掉,故平等耳。言行蘊中捨者,以行蘊念念遷流者,乃三毒習氣,薰發妄想,不覺令心昏沉掉舉。……故予教人參禪做工夫,但妄想起時,莫與作對,亦不要斷,亦不可隨,但撇去不顧,自然心安。蓋撇即行捨耳。」
釋「心所」條下,他說:「此心所法,又名心數,亦名心跡,亦名心路。謂心行處,總名妄想,又名客塵,又名染心,又名煩惱。……今修行人,專要斷此煩惱,方為真修。《楞嚴經》云:『如澄濁水,沙土自沉,清水現前,名為初伏客塵煩惱,去泥純水,名為永斷根本無明。』故修行人,縱得禪定,未斷煩惱,但名清水現前,而沙土沉底,攪之又濁。況未得禪定而便自為悟道乎。」此條他是以心所法作為考察禪定工夫的依準,而且主張,悟道須假禪定工夫。
釋「色法」條下,他說:「內五根,外六塵,通屬八識相分。故參禪必先內脫身心,外遺世界者,正要泯此相、見二分。……故身心世界不清,總是生死之障礙耳。」(註一九)
另外,紫柏大師真可曾說:「性相俱通而未悟達摩之禪,則如葉公畫龍頭角,望之非而宛然也。」(註二○)
註解
《卍續藏》八.三九六頁下。《卍續藏》八.四一九頁下。參考《華嚴經疏玄談》卷五(《卍續藏》八.五○五頁上─五一七頁下)。《大正藏》四八.四一五頁上。
《大正藏》四八.四一五頁下─四一七頁上。《卍續藏》九八.四二二頁下─四二三頁上。《卍續藏》九八.四二三頁上─下。《成唯識論俗詮》卷一及《成唯識論證義》卷一,均照抄《唯識開蒙問答》所說:「我佛法中,以心為宗,凡夫外道背覺合塵,馳流生死,菩薩改之,故造此論。」以說明《成唯識論》的成立宗旨。其實,「以心為宗」是《宗鏡錄》的立場,「背塵合覺」則出於《楞嚴經》卷四。而至於窺基的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卷一,乃謂:「諸愚夫類,從無始來,虛妄分別因緣力故,執離心外定有真實,能取所取。如來大悲,以甘露法授彼令服,斷妄狂心,棄執空有,證真了義。華嚴等中說一切法,皆唯有識。……故此即以唯識為宗。」(《卍續藏》七七.三頁下)《卍續藏》八二.九三頁上。《卍續藏》八二.三八九頁下─三九○頁上。《卍續藏》八二.三九二頁上。《卍續藏》八二.三九三頁上。《卍續藏》二二.二七二頁上─下。
《成唯識論集解》卷三(《卍續藏》八一.三九九頁上)。
《成唯識論集解》卷一○(《卍續藏》八一.六三六頁下)。《卍續藏》九八.五八三頁上。《卍續藏》七六.八五一頁下。智旭的《儒釋宗傳竊議》:
評窺基曰:「靈山道法,恐未全知,無怪乎《唯識》一書本是破二執神劍,反流為名相之學。」
評宗密曰:「則是荷澤知見宗徒,支離矛盾,安能光顯清涼之道。」(《靈峯宗論》卷五之三)《大正藏》四四‧四二二頁下。以上五例均見於《百法明門論論義》(《卍續藏》七六.八五三─八五七頁)。《卍續藏》一二七‧九一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