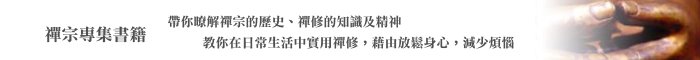大師語錄
南懷瑾說:堯舜禹三代的禪讓,在古文的記載上,明明告訴我們是“禪”,是“讓”……他們所以能夠如此做,當然道道地地可稱之為聖人的行為,又何必多此一舉,用後代世道人心的不古,而反證古人也必如後人的勾心鬥角,而且是必須要把它拉到和自己當代同樣的壞才算是合理?這豈不是讀書人思想上的癌症,是多餘的致命傷嗎?
經典回放
選自《孟子》
【原文】齊宣王問曰:“湯放桀,武王代紂,有諸?”孟子對曰:“於傳有之。”曰:“臣武其君可乎。”曰:“賊仁者,謂之賊;賊義者,謂之殘。殘賊之人,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,未聞弑君也。”
【譯文】齊宣王問道:“商湯王流放夏桀,周武王討伐商紂,有這回事嗎?”孟子對曰:“於傳有之。”孟子回答道:“文獻上有這樣的記載。”齊宣王又問:“臣子弑君,可以嗎?”孟子說:“敗壞仁的人叫‘賊’,敗壞義的人叫‘殘’;殘、賊之人,叫做‘獨夫’。我只聽說殺了獨夫紂,沒聽過弑君啊!”
大師釋疑
湯放桀:桀,夏朝最後一個君主,暴虐無道。傳說商湯滅夏後,把桀流放到南巢(據傳在今安徽省巢縣一帶)。
有諸:即“有之乎”,有這回事嗎?
武王伐紂:紂,商朝最後一個君主,昏亂殘暴。周武王起兵討伐,滅掉商朝,紂王自焚而死。
學儒一得:不為領導的愚蠢負責
孟子的“聞誅一夫紂矣,未聞弑君也”,可謂石破天驚,一下子過去的“湯武革命”以為後世的帝王定了性:講仁講義的才是帝王,不仁不義的就是獨夫民賊,殺之有理。這一真知灼見如果繁衍下去,未嘗不是中華之福,如果中國人都具有這種理念,帝王就不敢那樣為所欲為。可是不知為什么,此後變來變去,竟變成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這等於徹底否定了孟子的觀點。
孟子的觀點不傳,可能是不符合帝王的口味。那么一些無恥文人就會根據帝王的口味配置政治思想。據南懷瑾大師介紹說,朱元璋當了皇帝後,非常討厭孟子,他認為稱孟子為“亞聖“,實在不配,因此取消了孟子配享孔廟之位。不過晚年他閱曆多了,讀到《孟子》的“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勞其筋骨,餓其體膚,空乏其身,行拂亂其所為,所以動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恒過,然後能改;困於心,衡於慮而後作;征於色,發於聲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,出則無敵國外患者,國恒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,而死於安樂也”一節,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,認為孟子果然不失為聖人,於是又恢複了孟子配享聖廟之位。
在漢朝時,漢景帝曾親自一批儒、道兩派的學者“湯武革命”的合法性。有說合法的,也有說不合法的。最後發言的是曾做過司馬遷老師的黃生。他說:“帽子雖破,還要戴在頭上;鞋子雖新,還要穿在腳上。”這一觀點否認了“湯武革命”的合法性,應該是很合漢景帝口味的,如果大家都這么想,劉家天下就可以傳至千秋萬代了。這時,另一位學者反駁道:“這么說高祖不該斬蛇起義了?” 就是啊!如果“破帽子”必須戴在頭上,天下至今還是夏桀家的,根本沒有老劉家什么事,連周武王革命也可省掉。漢景帝見這個問題涉及到自己的祖宗,急忙下令:今後不准妄談湯武!
雖然不准談,“帽子雖破,還要戴在頭上”這一觀點還是成了政治思想的主流。所以中國人頭上的“帽子”總是“新三年,舊三年,縫縫補補又三年”,最後破得實在不像話了才拿掉換新。
實際上,帽子破了為什么還要戴在頭上,換新的不行嗎?為了美好形象,沒破也該換新。所以說,這條理論根本不通,只不過是拍帝王的馬屁而已!
現代社會不講“愚忠愚孝”,但要講忠誠敬業。應該忠誠到什么程度呢?古人有關忠誠的一些觀點很值得借鑒。
第一,忠誠的條件。
《說苑》認為:“君臣相與以市道接,君縣祿以待之,臣竭力以報之;逮臣有不測之功,則主加之以重賞,如主有超異之恩,則臣必死以複之。”意思是說:君臣關系可用市場交易的方式來處理,君王高懸俸祿對待臣子,臣子盡心竭力報效君王。臣子有了意外的功勞,君王就給他重賞。如果君王給予超常的賞賜,臣子就一定效死報答。
這就是說,按勞計酬是忠誠的起碼條件。
第二,忠誠的限度。
下屬跟領導“交易”的只是智謀體力,並沒有把人格、自由等等全部賣掉。而且下屬只需做分內的事,對分外的工作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做,沒有興趣也有權不做。
有一個故事:一個冬天的早上,晏子陪侍齊景公。齊景公覺得冷,請晏子弄點熱東西來吃。晏子拒絕道:“我不是管飲食的官員,請恕我推辭。”
齊景公說:“那么,請給我弄件皮衣服來。”
晏子說:“我不是管服裝的官員,請恕我推辭。”
齊景公說:“那么,你能幫我做什么呢?”
晏子回答說:“我是國家大臣。”
齊景公問:“什么叫國家大臣?”
晏子回答說:“國家大臣,能夠安邦立國,確定上下職守,使君臣的言行合宜;制訂百官次序,使各級官員適才適所;修訂條例法令,使之推行到全國。”從此,齊景公在晏子面前總是彬彬有禮。
有些領導不論公事、私事都安排下屬去做,下屬不知道這是過分要求,反而受寵若驚。那么,這就是給人家當家仆而非員工。
第三,不為領導的愚蠢負責。
在曆史上,不少昏君平時荒淫享樂,到了危難之際,卻要求臣子盡忠死節。這是讓別人為自己的愚蠢行為負責。
晏子曾就這個問題談過一個觀點。當時,齊王問他:“忠臣應該怎樣對待君王?”
晏子回答說:“君王危難時不犧牲,君王逃亡時不相送。”
齊侯不高興地說:“我封給他土地,賞給他高官厚祿,我有危難他卻貪生,我逃亡他卻拋棄我,可以說是忠嗎?”
晏子回答說:“大臣的正確意見能被采用,君王一輩子也沒有危難,有必要犧牲嗎?大臣的謀略能被聽從,君王一輩子也不會逃亡,有必要相送嗎?如果大臣的正確意見不被采納,君王有危難就隨便犧牲,這叫亂死;大臣的直言規勸不受重視,君王逃亡時卻假惺惺地相送,這叫虛偽。所以,忠臣應該讓君王采納正確意見而不是跟君王一起共赴危難。”
後來,齊王被權臣崔杼所殺,晏子並沒有為之死節。不過,在崔杼面前,他也表現出了寧死不屈的氣節。
孔子的弟子曾參的觀點也與晏子相似。他住在鄪城時,有一年,魯國將要攻打鄪城。曾子向鄪君辭行說:“我要暫時離開,等敵人走了再回來;請幫忙照看一下我的房子,不要讓豬狗進去。”
鄪君不高興地說:“我一向善待先生,沒有人不知道。現在魯國人要來攻打我,您卻要離開我,我為什么還要幫您照看房子?”
過不久,魯國人攻占了鄪城,並公布鄪君十條罪狀,其中九條是曾子平日跟他爭論過的。魯國軍隊撤走後,鄪君修好曾子的房子,親自去迎接他。
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。下屬已盡到責任,就不必為領導者的愚蠢行為負責。
第四,忠於國家、人民才是大忠。
忠於領袖,只是小忠。忠於無恥昏庸的領袖,只是愚忠。能夠為國家、為大眾盡忠竭力,才是真正的忠臣。
在五代十國時期,有一個名叫馮道的大臣,前後在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四個朝代十個皇帝手下做過官。很多人罵他無恥——只要盡一次忠,他早就該死了,可他竟然活著,還身居高位。
但馮道這個人有一個特點:無論在哪個皇帝手下做官,他都是一個廉潔愛民的好官,在百姓中聲譽很好。
馮道在後唐皇帝李嗣源手下做戶部侍郎時,父親去世,他回鄉守孝。期間家鄉鬧饑荒,馮道便將家裏的財物全部拿出來周濟鄉親,自己住在茅草屋裏,當地的官吏送來的東西他都沒有接受,當時契丹也仰慕馮道的大名,想出奇兵把他搶走,由於邊境防守嚴密,沒有得逞。
馮道後來被李嗣源任命為宰相。有一年,全國豐收,李嗣源很高興地馮道談起此事。馮道卻憂心忡忡地說:“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,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,經過井陘縣。那裏的地形非常險惡,路況又不好,崎嶇不平的,我深恐摔下來跌死,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韁繩,兩腿用力夾住馬身,小心翼翼地走,才僥幸沒有出事。等走過了這段險路,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,心理上放松了,手腳也放松了,不料卻狼狽地摔下馬來,跌了一大跤。所以我想到,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,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,大概更要時時留意。”
李嗣源被潑了一盆冷水,訕訕地問:“今年雖然豐收了,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?”
馮道說:“農家在歉收的凶年,很可能會餓死。如果豐收了,則所謂穀賤傷農,穀米多了,賣不出高價,還是吃虧受損。所以無論豐收或歉收,農民的生活都很苦。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:‘二月賣新絲,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,剜卻心頭肉。’這首詩雖然淺白,卻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,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,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,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。”
李嗣源是個大老粗,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,時常朗誦給他聽,以示不忘農民的疾苦。
馮道活到七十多歲,其一生大概可用他自己所說的兩句話來概括:口無不道之言,門無不義之財。像馮道這樣的人,大概從來沒有為哪個帝王死節的心情,但他能夠盡忠職守,能夠憂國憂民辦好事,就是一個大大的忠臣,比那些平時不作為,亡國了拼一死的所謂“忠臣”要貨真價實多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