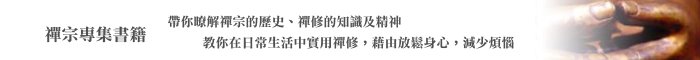正如我在上面講到的,l947年那篇文章遺留下來的關鍵問題是清音與濁音的對應問題。原來我認定了對音的來源是清音。周燕孫先生的解釋也是從這個角度上下手的。但是,時隔四十年,現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,我們大可以不必這樣去膠柱鼓瑟、刻舟求劍地去解決問題了。“佛”字的對音來源有極大可能就是濁音。
本來在回鶻文中“佛”字就作but,是濁音,這我在那篇論文中已經講過。可是我當時認為“佛”字是譯自吐火羅文,對回鶻文沒有多加考慮。這至少是一個疏忽。許多佛教國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歸命,在回鶻文中是:
歸命佛(南無佛)namobut
歸命法(南無法)namodrm
歸命僧(南無僧)namosa
在這裏,梵文buddha變成了but。回鶻文中還有一個與梵文buddha相當的字:bur。梵文中的dev tideva(天中天)在回鶻文中變成了t rit risiburxanA vonGabain,BuddhistischeT rkenmission,見 Asiatica,FestschriftFriedrichWellev,1954,OttoHarrassowitz,Leipzig,p 171 。burxan這個詞兒由兩個詞兒組成, bur, xan。bur就是buddha。這個詞兒約相當於吐火羅文A的pt k t(k s•s•i)和p tt k t(k s•s•i),B的pud kte或(k s•s•i)pud kte。
這個bur是怎樣來的呢?根據A vonGabain的意見,它是由but演變過來的。她認為,在中國北方的某一個方言中, t讀若 r,中國人把tatar音譯為“達怛”(古音以 t收尾),也屬於這個范疇同上書,頁同。。
H W Bailey對這個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。他說:
但是“佛”(Buddha)也用另一種形式從中國傳入中亞。西藏文h-bur表示出8世紀頃漢文“佛”字的讀音,參閱JRAS (《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》),1927年,頁296。這個 r代表從尾音 t發展過來的漢文尾音輔音。粟特文複合詞pwrsnk*bursang“佛陀僧伽”中有這個詞兒。這個詞兒從粟特文變成了回鶻文bursang,以同樣的形式傳入蒙古文。回鶻文(在蒙古文中作為外來語也一樣)burxan的第一部分,可能就是這同一個bur “佛”(參閱Mironov,《龜茲研究》,頁74)。於是回鶻文t ngriburxan意思就是“天可汗佛”,但是這個含義不總是被充分認識的,以致摩尼教回鶻文典籍中burxanzru cˇ意思是“Burxan瑣羅亞斯德”。在另一方面,日文借用了帶 t的字,Butu(Butsu)。OperaMinora,ArticlesonIranianStudies,ed byM Nawabi,ShirazIran,1981,p.104.
他對t>r的解釋同A vonGabain稍有不同。但是,這是從中國傳入中亞的,證據似還不夠充分。
上面我談了回鶻文中梵文Buddha變為but然後又由but變為bur的情況,其間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亞新疆的古代語言。我現在專門來談buddha在一些語言中變化的情況。我先列一個表:
大夏文buddha變成了bodo,boddo,boudo
拜火教經典的中古波斯文(巴列維文)
buddha變為bwt
摩尼教安息文buddha變為bwt/but/
摩尼教粟特文buddha變為bwtypwtyy
佛教粟特文buddha變為pwt
達利文buddha變為botG DjelaniDavary,Baktrisch,einW rterbuchaufGrundderInschriften,Handschriften,M nzenundSiegelsteine,Heidelberg,1982
從上列這個表中,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,這些文字大別可以分為兩類:一類是大夏文,在這裏,原來的梵文元音u變成了o或ou,此外則基本上保留了原形。一類是其他屬於伊朗語族的文字,在這裏變化較大。與梵文原字相比,差別很明顯:由原字的兩個音節變為一個閉音節,原字的尾元音 a(巴利文是 o,梵文體格單數也是 o)丟掉了。惟一有點問題的是,摩尼教粟特文語尾上有 y或 yy,可能代表一個半元音。即使是這樣,也並不影響大局, y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梵文 u相對應,它可能仍然是一個音節。至於在1947年那一篇論文中最讓我傷腦筋的清音濁音問題,在這裏已不再存在了。這裏絕大部分都是濁音,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。但是,根據H W Bailey的解釋,這也不是問題。他說:
在粟特文中,印度伊朗語族的濁輔音bdg在字頭上變成摩擦音 ,在含有bdg的外來詞中,它們都需寫成ptk。因此,pwty這個拼法就等於But 。在新波斯文中,but與這個形式正相當,意思是“偶像”。但是“佛”的含義在新波斯文許多章節中仍很明顯。OperaMinora,p.103.
這樣一來,清音濁音問題中殘留的那一點點疑惑也掃除淨盡了。
Bailey 還指出來,Bundhi nOperaMinorap.103。中有but這個字,它是企圖用來代表Avesta中的B iti這個字的(V d vd t,19,1,2,43,此章約寫於公元前2世紀中葉)。新波斯文證明有*Buti這樣一個字的,這個字與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應。學者們認為,這就是 Buddha“佛”。OperaMinorapp.106~107。
根據上面的敘述,1947年論文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全部徹底解決了。再同“佛”與“浮屠”這兩個詞的關系聯系起來考察,我們可以發現,第一類大夏文中與梵文Buddha對應的字,有兩個音節,是漢文音譯“浮屠”二字的來源,輔音和元音都毫無問題。第二類其他伊朗語族的文字中,與Buddha對應的字只有一個音節,Bailey在上引書,頁107,注2中指出,AvestaB iti最後的 i可能來源於東伊朗語言。這個 i就是我上面講到的半元音 y。是漢文音譯“佛”字的來源。難道這還不夠明確嗎?這個極其簡單的現象卻有極其深刻的意義。下面2中再詳細闡述。
我在這裏再談一談吐火羅文的問題。德國學者FranzBernhard寫過一篇文章:《犍陀羅文與佛教在中亞的傳播》G ndh r andtheBuddhistMissioninCentralAsia,A jali,PapersonIndologyandBuddhism,O H deA WijesekeraFelicitationVolume,ed byJ Tilakasiri,Peradeniya1970,pp 55~62.,主要是論證,佛教向中亞和中國傳播時,犍陀羅文起了極其重要的橋梁作用。他舉出“彌勒”這一個漢語音譯詞兒來作例子。他認為,“彌勒”這個詞兒是通過犍陀羅文Metrag a譯為漢文的。他在這裏順便提到“佛”字,並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論文:《浮屠與佛》。他說:
沒有提供一個詳盡的論證,我想指出,人們可以看到,漢文“佛”字音譯了一個古吐火羅文*but (可以和西吐火羅文‘pud kte’中的‘pud ’與東吐火羅文‘pt k t’相比)——由此可見,“佛陀”是一個次要的(晚出的)形式。
證之以我在上面的論述,Bernhard的構擬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。這也從正面證明了,我對“佛”字來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。“佛”字有沒有可能來源於伊朗語族的某一種語言?我認為,這個可能是存在的。這有待於深入的探討。我在這裏還想補充幾句。在同屬於伊朗語族的於闐塞文中,“佛”字是balysa ,顯然與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。見H W Bailey,DictionaryofKhotanSaka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197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