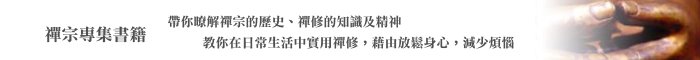一月。在息災法會修懺儀。至二十六日圓滿。主席林公。暨各長官蔣公戴公何公等。分設齋招待。蔣公詳細問法。條列唯物唯心。及神與基督之理。以書答之。在慈雲寺。華巖寺。上堂開示。侍者惟因筆記之。
〔附錄〕答蔣公問法書
(上略)佛教者。實今日週旋國際。趨進大同之惟一大教也。目下世界有兩種力——唯神論與唯物論。否認輪迴果報之說。故其影響所及。不可說。不可說。基督教之唯神論。雖有為善者神給與快樂報酬。為惡者神施以痛苦懲罰之說。然以神之存在。認為自然。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故不能令人深信。且貽唯物論者口實。此基督教所以不能維繫世界和平之故。實則神即是物。物即是心。心亦是神。然神亦非神。物亦非物。心亦非心。佛明三界《宇宙》本無一法《事物》建立。皆是真心起妄。生萬種法。「真心」亦不過因有妄物對待而立之假名。究其實。所謂真心亦非是。譬如大海。心是水。萬法《萬事萬物》是波浪。平靜者稱為水。洶湧者稱波浪。波浪平靜時仍是水。水洶湧時又成波浪。又因有洶湧之波浪。故稱不洶湧者為平靜之水。假使根本不有洶湧之相。波浪之假名固不能立。平靜之假名亦何由生。立亦不過吾人隨意立之假名。相信魚類或稱水為空氣。故知物即是心。有即是無。色即是空。妄即是真。煩惱即菩提。眾生即諸佛。一念迷惑時。心成物。無成有。空成色。真成妄。菩提成煩惱。諸佛成眾生。如水洶湧時即波浪。若一念覺悟時。物不異心。有不異無。色不異空。妄不異真。煩惱不異菩提。眾生不異諸佛。如波浪不洶湧時。仍是平靜之水。又因迷惑而起。物有色妄。煩惱。眾生。等對待。故立......心無空。真。菩提。諸佛。......等假名。若根本不有迷。則物。色。妄。有。煩惱。眾生。......等假名。固不能立。即心無空。真。菩提。諸佛。......等假名。亦何有立。所謂唯心唯物。有神無神。皆是識心分別計度耳。或云。「若是。佛學亦唯心論耳。」佛學雖說唯心。然與哲學上之唯心論懸殊。哲學上之唯心論。於心執有。於物執無。釋迦所謂以攀緣心為自性。執生死妄想。認為真實者。唯物論者。於物執有。於心執無。釋迦所謂顛倒行事。誤物為己。輪迴是中。自取流轉者。唯神論者。劃分物質實體。與神靈實體。為截然不同之兩個世界。釋迦所謂惑一心於色身之內。認一漚體。目為全潮者。各執偏見。或因近視。認牛之影像為牛。或以管窺牛。見牛角者則認牛角為牛。見牛頭者則認牛頭為牛。本無不是。弊在不見真牛全體。佛教則溯本窮源。將真實白牛清楚指出。若因指觀牛。未有不見真牛全體者。故欲救唯心唯物論之偏閉。捨佛教莫屬。
佛教所言明心性。《或稱常住真心,真如覺性,法身,實相...... 等皆是真理之別名》清淨本然。離諸名相。無有方所。體自覺。體自明。是本有自爾之性德。絕諸能《即今稱主觀主動等》所《即客觀被動等》對待。本無所謂十方。《東、南、西、北、東南、東北、西南、西北、上下、即今稱空間。》三世。《過去現在未來即今稱時間》更無所謂大地。人畜木石。地獄天堂等等。祇以妄立一念。致起諸有為法。《宇宙間萬事萬物》如『楞嚴經』《此經幾無法不備無機不攝,究佛學哲學者均不可不參究》釋尊答富樓那問。『覺性清淨本然。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』云。
『性覺必明。妄為明覺。覺非所(客觀)明。因明立所。(客觀)所既妄立。生汝妄能。(主觀)無同異中。熾然成異。異彼所異。因異立同。同異分明。因此復立無同無異。如是擾亂。相待生勞。勞久發塵。自相渾濁。由是引起塵勞煩惱。起為世界。靜成虛空。虛空為同。世界為異。彼無同異。真有無法。』
『覺明空昧。相待成搖。故有風輪。執持世界。因空生搖。堅明立礙。彼金寶者。明覺立堅。故有金輪。保持國土。堅覺寶成。搖明風出。風金相摩。故有火光。為變化性。寶明生潤。火光上蒸。故有水輪。含十方界。火騰水降。交發立堅。溼為巨海。乾為洲潬。以是義故。彼大海中。火光常起。彼洲潬中。江河常注。水勢劣火。結為高山。是故山石。擊則成燄。融則成水。土勢劣水。抽為草木。是故林藪。遇燒成土。因絞成水。交忘發生。遞相為種。以是因緣。世界相續。(星雲之說恐亦不及此說之詳)』
『復次富樓那。明妄非他。覺明為咎。所妄既立。明理不踰。以是因緣。聽不出聲。見不超色。色香味觸。六妄成就。由是分開見聞覺知。同業相纏。合離成化。見明色發。明見想成。異見成僧。同想成愛。流愛為種。納想為胎。交遘發生。吸引同業。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雲。(胞胎中受生之質)等胎卵溼化。隨其所應。卵為想生。胎因情有。溼以合感。化以離應。(佛在二千多年前指出)情想合離。更相變易。所有受業。逐其飛沈。以是因緣。眾生相續。』
『富樓那。想愛同結。愛不能離。則諸世間父母子孫。相生不斷。是等則以欲貪為本。貪愛同滋。貪不能止。則諸世間胎卵溼化。隨力強弱。遞相吞食。是等則以殺貪為本。以人食羊。羊死為人。人死為羊。如是乃至十生之類。死死生生。互來相噉。惡業俱生。窮未來際。是等則以盜貪為本。汝負我命。我還汝債。以是因緣。經百千劫。常在生死。汝愛我心。我憐汝色。經百千劫。常在纏縛。惟殺盜婬。三為根本。以是因緣。業果相續。』
『富樓那。如是三種顛倒相續。皆是覺明明了知性。因了發相。從妄見生。山河大地諸有為相。次第遷流。因此虛妄。終而復始。』
真如覺性。既立真妄。於是有不變與隨緣之別。平等不變。離差別相。無聖無凡。非善非惡。真實如常。不變真如也。隨緣生滅。起差別相。有聖有凡。有善有惡。隨緣真如也。就不變真如言。萬法即真如。非心非物。非神也。就隨緣真如言。真如即萬法。即心即物。即神也。唯心論者。錯認識神。就隨緣真如。以為即是真心。而倡唯心論。唯物論者。囿於邊見。就隨緣真如。即物之見。而倡唯物論。又據唯物而倡無神論。唯神論者。亦囿於邊見。妄生分別。就隨緣真如。即物與神之見。而倡唯神論。殊不知心即物。物即神。心物與神同一理體有物則有心有神。無心則無神無物。然此「有」非有無之有。乃非有而有之妙有。此「無」非斷絕之無。乃超有無之妙無。《此妙「有」妙「無」與下說之,無生之生與有生之生,其義頗奧,非語言文字可到,故為禪門要關。》唯心論。唯物論。唯神論者。均未明斯義。互相攻擊。實則皆無不是。亦皆非是。一研佛學。自可渙然冰釋矣。
佛學對於宇宙本體之研究。除前述外。其他對於世界之構造與成壞。人身器官之組織。及其他種種問題。在『楞嚴經』及諸經論。多有詳細論列與說明。且大多與後來哲學科學發見者相合。現未及詳指。其於人生價值。則大菩薩之行願。已非他聖賢可及。經典上在在處處可見之。於此可知佛教之神妙及偉大處。然佛教絕非標奇立異以衒人。亦非故弄玄虛以惑眾。其一言一行。皆從戒定慧三學親履實踐得來。何謂戒定慧。防非止惡曰戒。六根涉境。心不隨緣曰定。心境俱空。照覽無惑曰慧。防止三業之邪非。則心水自澄明。即由戒生定。心水澄明。則自照萬象。即由定生慧。儒家亦有「定而後能靜。靜而後能安。安而後能慮。慮而後能得。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」之言。即哲學家亦莫不沈思竭慮以從事所學者。然儒者及哲學科學者。則以攀緣心。思宇宙萬物。不知宇宙萬物。亦是攀緣心所造成。能慮所慮。俱是攀緣心。欲而探求真理。等於趺坐椅上。欲自舉其椅。勢不可能。此今哲學者。對於認識論聚訟紛紜。莫衷一是。終無結論者。因此故也。佛則離言絕慮。以智慧覺照宇宙萬事萬物。如下座舉椅。故任運如如。此佛教括哲學。科學。宗教三者。一爐共冶。又皆先知先覺者。蓋有由來也。日本以佛為國教。近世之興。其維新諸賢。得力於禪學不少。為眾所週知之事。若非其軍閥迷信武力。與道全乖。以殺戮為功。以侵略為能。安有今日之敗。
或疑佛教為消極為迷信。不足以為國教。此特未明佛教者之言。實則佛法不壞世間相。豈是消極者。佛法步步引人背迷合覺。豈是迷信者。考佛梵名佛陀義譯覺者。自覺覺他。覺行圓滿。謂之為佛。菩薩梵名菩提薩埵義譯覺有情。有出家在家二種。乃發大心為眾生求無上道。一面自修。一面化他者。其積極與正信。恐無有出其上。佛教依折攝二義。立方便多門。何謂折。折者折伏惡人。昔石勒問戒殺於佛圖澄。澄曰。「子為人王。以不妄殺為戒殺義。」蓋在家大權菩薩。為折惡利生故。雖執刀杖。乃至斬其首。於戒亦無犯。反生功德。因惡意而殺人。皆知不可。因善意而殺人。固是在家大權菩薩之金剛手眼也。何謂攝。攝者攝受善人。佛菩薩為利益眾生。故不避艱危。有四攝法。一。布施攝。若有眾生樂財則施財。樂法則施法。使生親愛心而受道。二。愛語攝。隨眾生根性而善言慰喻。使生親愛心而受道。三。利行攝。起身口意善行。利益眾生。使生親愛心而受道。四。同事攝。以法眼見眾生根性。隨其所樂而分形示現。使同其所作霑利益。由是受道。佛菩薩之積極為何如。
何謂方便。方便者量眾生根器施諸權巧而渡之也。前述之四攝法。亦是方便之門。法華經化城喻品云。『譬喻險惡道。迴絕多毒獸。又復無水草。人所怖畏處。無數千萬眾。欲過此險道。其路甚曠遠。經五百由旬。時有一導師。強識有智慧。明了心決定。在險濟眾難。眾人皆疲倦。而白導師言。我等皆頓乏。於此欲退還。導師作是念。此輩甚可憫。如何欲退還。而失大珍寶。尋時思方便。當設神通力。化作大城廓。汝等入此城。各可隨所樂。諸人既入城。心皆大歡喜。此是化城耳。我見汝疲極。中路欲退還。權化作此城。汝今勤精進。當共至寶所。』......觀此可知釋尊分時設教。權施方便之深意。故最上根者與言禪。上根者與言教。重分析者與言唯識。普通者與言淨土。權設大乘小乘。不論出家在家。務求普化群機。使一切眾生。咸沾法益也。近人觀佛子之對像跪拜。及淨土之持名念佛。即以其無神論立場。謂為迷信。不知跪拜與對長上致敬何異。念佛對於修心有莫大之功。且持名念佛。不過方便初機之簡捷法門。更有觀像念佛。觀想念佛。實相念佛等法門。淨土自有無窮妙用者。人自不會耳。豈迷信哉。
或謂。基督教亦脫胎於淨土宗『阿彌陀經。』試觀耶穌身上搭衣。與佛相同。阿彌陀經說西方極樂世界。耶氏亦說天國極樂。淨土往生分九品。耶教李林天神譜。亦言天神分九品。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耶氏亦言你不在人間立功。上帝不許你到天國。淨宗二六時念佛名號。求佛接引。耶氏亦以早晚祈禱上帝哀祐。至佛門有灌頂之法。耶氏亦有洗禮之儀。——觀此耶氏教義。與淨土宗趣。大致相同。而耶氏誕生於釋迦後千有餘年。當是曾受佛化。得阿彌陀經之授。歸而根據之。另行創教。似無疑義。且耶氏曾晦跡三年。當是赴印度參學。事雖無據。而跡其蛛絲馬跡。似非厚誣云云。其言良非向壁虛構。不過表面上看來。耶氏雖類似淨宗初機之持名念佛。實際則遠遜之。耶教著於他力。明其然。而不明其所以然。跡近勉強。持名念佛。則重他力自作相應。如楞嚴經大勢至圓通章云。...... 『十方如來。憐念眾生。如母憶子。若子逃逝。雖憶何為。子若憶母。如母憶時。母子歷生。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。憶佛念佛。現前當來。必得見佛。去佛不遠。不假方便。自得心開。......我本因地。以念佛心入無生忍。今於此界。攝念佛人。歸於淨土。』有因有果。故理事無礙。且耶教說永生。淨宗則云往生淨土。見佛聞法。悟無生忍。永生之生。以滅顯生。有生對待。終有滅時。無生之生。則本自無生。故無有滅。此所以稱為無量壽《阿彌陀譯名》也。
願行菩薩行求無上道者。非必出家而後可行。在家亦無不可。不過出家所以別國主。離親屬。捨家庭者。意在脫離情欲之羈絆。捨私情而發展佛力之同情。捨私愛而為偉大之博愛。以渡一切眾生為忠。以事一切眾生為孝。此大同之義也。孫中山先生嘗曰。「佛教乃救世之仁。佛學是哲學之母。宗教是造成民族。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。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。研究佛學。可補科學之偏。」今公亦以佛教之輸入中國。有裨益於中國之學術思想。故稱佛教為今日之週旋國際。趨進大同之唯一大教。豈徒言哉。且今日信教自由。不能強人以迷信。祇可令人心悅誠服而生正信。然則捨佛教其誰與歸。(下略)
〔附註〕 惟因書記曾告編者曰。師由重慶回時。各鉅公均贈以名貴古玩寶玉。及字畫等。其數多至五大箱。師於沿途分贈與人。惟因問之。師曰。「徒費保存。徒亂人意。」遂不留一物。沿途歸依者有四千餘人。所收果資。亦一一令惟因登記。撥修建海會塔云。
三月回南華。修七眾海會塔。掘地為塔基。出古棺四。長一丈六尺。中空無骨殖。幽宮磚。每尺八寸餘。多花紋。及鳥獸。間有干支字。然無年代可考也。六月設戒律學院。以教青年僧眾。又於寶林門內辦義務小學。收教鄉村貧民子弟。冬月海會塔成。湯瑛為文記鐫石。
〔附錄〕南華寺七眾海會塔記
湯 瑛
荼毗為四大葬法之一。西竺古制也。自大教東來。四眾悉依。明代尤盛。逮清而稍替矣。粵中叢林間亦有普同塔之建。然乏閎構。民二十三年虛雲老和尚卓錫南華。即欲籌建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及式剎摩那尼等。七眾海會塔。並建佛殿僧舍。薰修持誦。普利幽冥。時以祖庭傾圮。百廢待興。建設數年。未遑并舉。至癸未春。得潮洲鄭子嘉居士相助。始克完竣。而此事因緣之奇。昭靈之感。有不可不記者。初居士僑商香港。為巨室。民國三十年冬。香港淪陷。閭閻騷然。人且相食。惶惶然不終日。居士夜夢武士披甲擎杵。示以避逃方所。醒而識之。挈眷急行。沿途危難。皆化險為夷。若有神助。歷時兼旬。路經南華寺下車歇息。信足遊覽。至天王殿後。仰瞻韋馱菩薩像。則赫然夢中所見之武士也。居士駭愕。五體投地。感極而泣。乃詣方丈。謁虛雲老和尚。且白其異。並發心歸依。願損資造寺。用報菩薩加被之恩。雲公以南華殿宇大致竣工。乃語缺海會塔事。居士聞命踴躍。立捐國幣五萬元。其折。嗣應時。亦銳任勸募。周懷遠居士聞風隨喜。亦助二萬元。張子廉居士助一萬元。同為之倡。其後善信接踵捐助。斯塔莊嚴。遂爾從地湧出。計始於癸未春。竣工於本年臘月。共費國幣約百餘萬元。捐款芳名。另勒碑石。鳥虖。諦觀鄭居士如上因緣。韋馱菩薩。固屹然未嘗少動也。豈祇韋馱菩薩未少動。即我佛如來。乃至虛雲老和尚。亦未嘗少動也。經云。『隨緣赴感靡不周。而恆處此菩提座。』佛法之不可思議。豈在纏縛凡夫所能測度也。鄭居士以宿世善因。獲茲善果。隨緣清信。又因斯善果。而植善因。萬善齊彰。同圓種智。是宜操觚記實。以詔來茲。
〔附記〕 湯瑛於癸巳年春在香港出家。法號融熙。旋赴南洋弘法。己亥寂於 吉隆坡。
又予於是冬將移錫雲門寺。乃作重興南華寺記。
〔附錄〕重興曹溪南華寺記
虛 雲
於一毫端現寶王剎。坐微塵裏轉大法論。盡虛空。遍法界。何處不是道場。一累土。一畫沙。何事而非佛事。語其極則。動念即乖。寧有語言文字可記載耶。然而世有遷流。界有方位。道有隱顯。事有廢興。況夫道在人弘。理因事顯。欲承先而啟後。續慧命以傳燈。又烏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耶。曹溪為六祖大鑑禪師道場。傳東山法脈。弘南頓宗風。一滴曹溪。灑遍寰宇。五宗競秀。千載嚮風。若闇。若彰。成佛成祖者不知若干人。報本思源。丕顯奕世。不綦重哉。是則更不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也。雲老矣。耄齡始得來曹溪為六祖作掃除隸。追懷往事。若有夙緣。十載經營。綜理次第。心力交瘁。始具規模。後之僧徒。守此勿失。永保道場。上以微報佛祖之大恩。外亦不辜護法之宏願。是雲所以望諸來者。
中華民國七年歲次戊午。雲在滇南雞足山時。李公根源督辦韶州軍務。修理南華寺。訊至滇。屬雲來主持斯事。雲以雞山因緣未竟。謝卻之。民國十七年戊辰。雲與王居士九齡同寓香港。時粵主席陳公銘樞。邀至珠江。亦請雲住持南華。而先有海軍部長楊樹莊。方聲濤等。以閩之鼓山寺。急待整理。派人挾伴雲往。雲以出家鼓山因緣。勿能卻也。遂之鼓山。數載辛勞。略有建制。至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四月。粵僧敬禪。之清。福果等。參禮鼓山。屢言粵中佛法衰落。祖庭傾圮。欲雲赴粵中興之。意未決。一夜連獲三夢六祖。喚來南華。次日向諸人敘述夢緣。感歎希有。不數日粵北綏靖主任。今省府主席。李公漢魂。電函邀約。住持南華。眾亦以夢境敦勸。雲意動。即擬三事。復李公相商。(一)六祖道場南華寺。永作十方叢林。任僧棲止。(二)宜徵取原有子孫房眾願意交出。不可迫脅。(三)所有出入貨財。清理產業。交涉訴訟等事。概由施主負責。倘允三事。即來參看。李公復電照行。並派吳祕書種石。暨廣州香港緇素十餘人。到鼓山迎迓。雲遂赴粵。詣曹溪。禮祖庭。觀察形勢。左右閉隔向背失宜。因謂李公曰。「此事實費躊躇。貧僧力薄。恐不勝任矣。」李公曰。「何謂耶。」雲曰。「此係宇內名勝祖庭。今頹廢若此。非掀翻重建。不足暢祖源而裕後昆。若作成次序如法。亦非歷數年工程。費數十萬金不辦。貧僧安有此力哉。」李公曰。「師勉任之。籌款我當盡力耳。」命繪圖參酌。雲以重念祖庭故。遂許之。時正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。祖師聖誕節也。乃解辭鼓山職務。鞠躬盡瘁。以事祖庭。先相度全山形勢。考天監初。智藥尊者。化曹侯開山。建寶林禪寺。其基地似在左邊。即今南華精舍之下。至唐儀鳳初年。六祖來此。已閱一百七十年。舊寺久廢。山場亦歸陳姓管業。六祖欲恢復舊寺。時陳亞仙之先人墳地。已葬寺之右邊矣。六祖感動四天王定界。亞仙乞留祖墓。保存至今。故當日六祖造寺。其寺牆外為陳亞仙祖墳。墓右悉為龍潭。六祖降龍蛻化。欲堙其潭。以建僧舍。工未半而祖入滅。後弟子奉祖肉身。築塔於亞仙祖墳前。初為木塔。不甚高也。至憲宗元和七年。賜諡大鑑禪師。塔曰元和靈照。稍加修飾。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。詔新師塔七層。易以磚石。塔曰太平興國之塔。以後歷代修繕。皆沿其址。(後人觀察浮圖高聳。壓亞仙祖墳。未詳此一段經過事實。)以形勢言。該塔壓寺右臂。伸縮妨礙。以百房子孫至明代而僅存十餘房。讀南華事略。不禁掩卷三歎。萬曆二十八年。庚子秋。憨山清公。始入山重興祖庭。意欲填築龍潭。統一各家方位。糾正山向。閱時八載。工程及半。以魔事去。後雖重來。不久示寂。讀夢遊集誓願文。冀後輩重興。滿其素願。迄今又越三百餘年矣。清代康熙年間。雖經平南王尚可喜重修。納形勢家言。填塞龍潭。將全寺殿堂。移置陳亞仙祖墳右。而靈照寶塔又壓住寺之左臂。且也。卓錫泉出自象口。寺後橫山是象牙。乃本寺之主靠山。自憨山挑培以後。歷次修繕者。不審山脈。削去靠山。使飛錫橋水直衝寺後。形成洗背水。此一忌也。龍潭之右小岡。形似象鼻。係寺內之白虎山。挖斷數處。包圍不密。缺乏遮蔽。此二忌也。外往渰溪路之山坳。破缺多處。正當北風。又無叢林掩護。此三忌也。寺之前後靠向不正。舊日頭進山門。即在現今西邊大樟樹林內。中有深坑。如現今之曹溪門前。墓地坵陵起伏。穢積亂葬。坎坷寓目。幽明不安。此四忌也。雲海樓下之井。名羅漢井。在舊天王殿西邊。井右有一高坡。逶迤達天王殿門口。成為白虎捶胸格。此五忌也。寺後大山。雖號雙峰。其實太弱。更因寺之坐靠。不依正主。以凹窪為背。是以子孫日漸衰弱。雲至曹溪。房分只有五家。其數。不上十人。不居寺內。各攜家眷。住於村莊耕植牧畜。無殊俗類。其祖殿香燈僧。歸鄉人派管。每逢二八兩月祖誕。所有收入。由鄉村管理。宰殺烹飲。賭博吸煙。人畜糞穢。觸目掩鼻。視憨山所記當日情形。尤有甚焉。夫以我六祖大鑑禪師。道侔千佛。德被含生。固足以耀後世而垂無窮。獨於其肉身所在道場。區區咫尺之地。輒不及百年而即中落者。雖曰人謀之不臧。要亦未嘗非地形之失利。相其陰陽。觀其流泉。岩虛語哉。雲察勘既竟。商諸李公。先定山場。以圖展布。李公與吳君種石。將寺屬基地。創辦林場。劃出寺外四週。山地五百畝。交寺建築。雲不得不殫心竭力。從事建置。初雲入山時。除祖殿寶塔及蘇程庵一那份稍為完整外。其大殿經樓方丈僧寮均皆摧朽。容眾無所。暫搭杉皮茅蓬二十餘間。作大寮客堂。及緇素工人食宿處。乃著手先行培修祖殿。殿內祖坐木龕。以年遠故。被白蟻損壞。乃請出祖師肉身聖像。重新裝修。另照育王塔式。作祖坐龕。龕外塑南嶽。青原。法海。神會。四位侍側。以南嶽。青原。為祖在日之上首弟子。五宗皆由二派流出。法海則流通祖師法寶。神會在滑臺大振頓宗。若孔門之四哲也。復在祖殿兩廂建東賢殿。西賢殿。塑五宗有功法門諸祖。若孔門之七十二賢也。曹溪為禪門洙泗。應先正名定位。原先殿左供聖父聖母右供伽藍神。中製靈通侍者酒亭。比憨山公當日戒靈通飲酒時。尤變本加厲焉。又憨公肉身。原供靈照塔內。有一四尺餘高之銅鑄觀音大士。供在憨山下位。序次失儀。而丹田肉身。原供祖殿東廂。已為駐兵之所。積穢不堪。雲乃先建報恩堂。安奉聖父聖母。於祖龕之左。另製一龕。以奉憨山。右製一龕。以奉丹田。建伽藍殿。以奉伽藍神。儕靈通侍者於內。撤其酒亭。(另為文祭告。)又於祖殿之西。建觀音堂一所。共十五間。建外眾圊及雜屋九間。內眾圊及浴房七間。移奉靈照塔內之觀音大士。并為女眾受戒挂搭之所。將方丈內之六祖銅像。供於靈照塔內。(此像原在韶州大鑑寺。因寺燬。乃移奉南華。)祖殿之後。舊名蘇程庵。積穢充滿。清除修建。架以履樓。通連祖殿。暫作方丈。方丈之東。為一土坡。將土挑培主山。築樓房上下各五間。以作祖堂。供歷代祖師及南華繼席宗匠牌位。方丈之西。即新建之觀音堂也。內部情形。略為就緒。雲乃預期十事。次第進行。
(一)更改河流以避凶煞
考曹溪河流。由東天王嶺。繞出寺前。西達虹光橋。以入馬壩。寺門距溪邊約一百四十餘丈。因年遠失修。沙石壅塞。溪水改向北流。直衝寺前大路邊。向寺門激射。此反弓格也。故必先更改河流。恢復舊道。以避凶煞。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夏。勘定水線。計挑築新河。填補舊河。全程共八百七十餘丈。所費甚巨。正擬動工。乃於七月二十日夜雷雨大作。水漲平堤。沖開新河。舊河已被泥土淤塞。砂石湧起。反形成寺前之一字案。此護法神之力也。雲何功焉。今寺前林木蔥鬱。沙環水帶。非復曩時景象矣。
(二)更正山向以成主體
查舊日山門在樟樹西邊。越過深坑乃得出入。不成門面。而現在山門外之大路坪場。坡陀歷亂。野葬縱橫。因此先遷葬亂墳。挑平土石。即以土石築成左右護衛山。高有數丈。以其基地改為曹溪正門。外闢廣場。栽種樹木。緣蔭翳天。白雲覆地。望之儼然一清淨道場。
(三)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築高左右護山以成大場局
寺所枕山。形像似象。後人將方丈後之靠山。分段剷去。使寺後落空無主。寺坐象口。其左右係象之下頷。夷成平地。陰陽不分。其右係象鼻。應當高聳。分節起伏。又被人在毗盧井處切斷。(井在今禪堂後西角。)一路挖平。直到頭山門。成大空缺。又無樹木擁護。遠望孤寺無依。近察鼻節已陷。殊痛恨也。雲於拆平舊殿堂及丹墀時。所有土石。悉歸三處。右高於左。形象鼻也。稍曲而東。形鼻之捲也。中鑿蓮池。象鼻之吸水處也。培高後山。依倚固也。三處皆栽林木。今幽翠矣。
(四)新建殿堂以式莊嚴
民國二十五年丙子。新建大雄寶殿。按舊日殿基。在現今之功德堂後。靈照塔壓其左臂。其方向為坐艮向坤。平藩尚可喜所建也。雲以大殿為全寺主體。關係重大。乃相度地勢。鳩工備材。移大殿於塔前。即以靈照塔作殿之靠背。去壓臂之患。獲端拱之安。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線。將與寶林門同一方向。既協定星。復觀大壯。堂堂正正。燁然巨觀。外像象王之居。中施獅子之座。塑五丈高金身大佛三尊。迦葉阿難二尊者侍側。四週塑五百羅漢。左右文殊普賢二菩薩。座後塑觀音大士。使尋聲而至者。覿面相呈。慕曹溪而來者。飽嘗而去。築殿基時。土中挖出鐵塔一座。高尋丈。為清代雍正時造。——志書載為降龍塔。非也。移鐵塔於鼓樓下。金飾而莊嚴之。復將平藩二碑。分嵌於鐘鼓樓內。以備考古。同時挑平今曹溪門地基。及門口之亂坡。砌洩水溝五十餘丈。自象鼻岡下穿過山隈。挖成水洞。注入曹溪門內水池。池週四十餘丈。中建五香亭。其形如象鼻之捲蓮花也。鱗甲之類。以棲息焉。廿六年丁丑。建曹溪門。(原昔曹溪門在西邊大樟樹下。)現稍移東。取坐癸丑向丁未六度兼癸丁線。與四天王殿同向。舊日天王殿。在今之西歸堂後。今之殿址多為亂坡。夷平之下。以建四天王殿。其左為虛懷樓。右為雲海樓。復建香積廚齋堂。庫房等屋宇。建香積廚時。土中挖出千僧大飯鍋一具。元代物也。移置大殿後觀音菩薩座前。以植蓮花。廿七年戊寅。建寶林門。其原址在現今西邊空缺處。坎坷不平。乃挑其土以培高左右沙手。雲海樓下有一古井。名羅漢井。原在深坑內。加高一丈另五寸。使與園地平衡。中闢神道。左右各築蓮池。重建鐘樓。此銅鐘為宋代物。埋土中。出而懸之。聲聞十里。發人深省也。又建報恩堂。伽藍殿及客堂。廿八年己卯。建鼓樓。祖師殿。供東土初祖以至六祖。及本寺開山智藥尊者七位。又建西歸堂。安僧眾覺靈。建功德堂。奉各護法主位。建雲水堂。接待來往僧眾。廿九年庚辰。建禪堂。依制坐香。建韋馱殿。班首寮。維那寮。以嚴督察。又建如意寮。置備醫藥。以調養病苦。指定售南華茶葉入款。以為湯藥之費。又鑿通方丈後山。引導卓錫泉水源。砌成水洞。安置總分鐵管。直透香積廚。及各堂寮。三十年辛巳。將大殿之後。靈照塔之前。建法堂一座。其上為藏經樓。內藏廿五年由北京請回龍藏全部。大藏遺珍全套。又李伯豪主席送磧砂藏一部。築戒壇時,在土內挖出萬曆年修塔碑。豎立雨花臺壁中。建迴向堂。安奉國殤忠魂。建迎賢樓。招待來往賓客食宿。建無盡庵。以為女眾清修。(按無盡藏尼。為六祖最初護法。其庵址似在卓錫泉右邊。憨山祖師曾經重修。傾廢已久。雲以庵與寺太近。故清出離寺東約三里許之柏樹下村莊房。榜曰古無盡庵。移女眾於此修持。至無盡尼之真身。現在曲江灣頭村西華庵。今依其形貌。塑像一尊。供於庵中。以作女眾修持模範。)三十一年壬午。於左殿左邊建念佛堂。以安修淨土者。掘地時得萬曆年余大成蘇程庵碑。足資考據。豎立於念佛堂照牆內。又建延壽堂。安諸老人。平地基時。發現宋淳熙年間所刻六祖真像及碑銘。移存祖殿照壁廊內。又在鐘樓之後。建碾米房。沐浴室。工行寮。儲蓄所及東圊。於其地掘出無數人骨。及一丈六尺之杓棺數具。其中火坯之穀類甚多。待考證也。三十二年癸未。建海會塔。於寺東二里許。緣南華舊無普同塔。歷代亡僧。隨山亂葬。日久遂形拋露。莫慰先靈。乃先設荼毗爐。以梵遺蛻。嗣建斯塔。以藏七眾。該塔用鋼筋水泥築成。堅固異常。足納灰塔數百萬具。其上建念佛堂。長年念佛。以利冥陽。於塔左右各建樓房四五楹。以為看塔念佛人住所。又於塔前圍築圍場。遍栽林木。門外鑿一方池。以植蓮花。又重修卓錫泉。因舊日無池蓄水。飲料不潔。乃鑿池蓄水。中隔砂井。施以藥物。用鐵管引入大寮。又修飛錫橋。以保存古蹟。修伏虎亭。以弭虎患。又因曹溪各村貧苦兒童。無力就學。因設義學教之。此民國三十二年事也。綜上十年。雲重新祖庭。至此始成具體。茲再條析述之。綜覽全局。計自曹溪門至卓錫泉。由南至北。深一百五十一丈。由東邊寺牆至禪堂西壁。廣三十九丈五尺。首進曹溪門上下各一楹。越圍坪。度放生池。中有五香亭一座。次進為寶林門。樓上下各五楹。歷神道至陛階。至四天王殿五大楹。殿左為虛懷樓。上下各五楹。殿右為雲海樓。上下各五楹。均南向。由韋馱殿經花園。上丹墀。大雄寶殿五楹。殿後法堂戒壇。及藏經閣上下各五楹。法堂之後為靈照塔。塔後為祖殿。殿後為方丈。上下各五楹。方丈後繞道依山。至飛錫橋伏虎亭。以達卓錫泉。此中路也。東邊由虛懷樓後。報恩堂樓上下各二楹。鐘樓三層各一楹。伽藍殿上下各五楹。客堂樓上下各五楹。齋堂樓上下各五楹。庫房樓上下各五楹。歷階至迴向堂五楹。迴光堂五楹。延壽堂樓上下五楹。進為念佛堂樓上下各五楹。均西向。至祖堂樓上下五楹。則南向矣。此東路也。西邊至雲海樓後。西歸堂樓上下各二楹。鼓樓三層各一楹。祖師殿樓上下各五楹。雲水堂樓上下各五楹。西入禪堂五楹。南向。韋馱殿。維那寮共七楹。北向。班首寮。如意寮各七楹。東西向。再上為西圊。計外堂廁所及雜屋共九楹。內堂廁所及沐浴室七楹。進為返照堂五楹。經祖殿兩傍建東賢殿三楹。西賢殿後達觀音堂。共計樓上下各十五楹。此西路也。附於東路者。為客堂後之待賢樓。上下各五楹。齋堂之後。香積廚五楹。沐室七楹。碾米房一楹。工人室三楹。柴草寮五楹。東圊五楹。隸屬寺管者。無盡庵三十八楹。海會塔正座樓上下各三楹。兩旁樓房各四楹。幼幼亭右守望所三楹。總計新建殿堂房宇庵塔約二百四十三楹。其中間隔各部分寮房若干間。亦足以暫容清修勝侶矣。又塑造大殿及兩序大小佛像。共計約六百九十尊。備極莊嚴。
(五)驅逐流棍革除積弊
雲自甲戌八月入山。見聖地道場。變作修羅惡境。祖庭成牧畜之所。大殿為屠宰之場。方丈作駐兵之營。僧寮化煙霞之窟。菩提路列肉林酒肆。袈裟角現舞扇歌衫。罪穢彌倫。無惡不作。雲始以善言相勸。置若罔聞。稍示權威。則持刃尋逐。瀕於生死者亦屢矣。終仗護法大力。切實嚴禁。督警驅除。與之爭持。歷三四年乃掃除淨盡。復於寺外大路以南。蓋板屋十餘間。遴選善人。販賣茶果。祇許素食。均能奉持。以至於今。得以重興殿宇。莊嚴淨域也。
(六)清丈界址以保古蹟
自祖師募化檀越陳亞仙捨地。以四天王嶺為界。千載以來。已成定案。第因年代久遠。人事變遷。雖志書所載甚詳。而實際反空無所有。僧餘破壁之參。佛久積塵之坐。尺天寸地。指點無從。至民國廿五年丙子九月。請省府令行派員履勘劃界。保存古蹟。繪圖立案。出示曉諭。照圖管業。使界址復明。
(七)增置產業以維常住
查南華寺產。志書所載甚多。歷經豪右併吞。奸僧盜賣。雲入山時僅有租穀二十擔。千分不逮一也。乃著手整頓。擬先清理產業。調驗契據。如無紅契。而屬寺產者。不容侵佔。有紅契而原屬寺產者。准以七成贖之。正計劃中。而時局屢變。風波動盪。無從進行。祇有從前北區綏靖處所辦之林場。於民國廿五年由政府批准。交回寺內管業。惟所入無多。不足以贍常住。雲至乃募資漸次收買。至民國廿八年連贖回及新買之稻田若干畝。每年租穀約數百擔。(另詳香火田產記。)至是常住始有粒食可靠。然所歷艱苦。不可言喻。(其最苦者厥為後山紫筍莊寺田三百數十坵。為黎謝二姓所侵佔。被人從中舞弊。向政府交涉。又因時局變遷。迄未清回。望後來者有以收回之。)
(八)嚴守戒律以挽頹風
昔我佛入滅。垂誡後人以戒為師。嚴規行也。今雖末法。僧伽墮落。粵中尤甚。顧念南華為宇內祖庭。豈容污合。今茲冷灰再煙。非宏法不能重興。非守戒不能宏法。雲乃遵百丈清規。嚴肅綱紀。一粥一飯。持午因時。一步一趨。悉守儀範。為真佛子。乃可保叢林於久遠也。(其各種條規。另見同住規約。)
(九)創禪堂安僧眾以續慧命
初祖西來。單傳直指。六祖得法。弘揚五宗。禪波羅蜜也。五燈會元所記諸佛諸祖無不自禪定中來。得大機大用。渡眾無算。今我六祖頓教道場。寂寞久矣。雲乃造禪堂。定香數。發警策。下鉗槌。冀其磨練身心。渡己渡人。以續我佛慧命。(課程另見規約)
(十)傳戒法立學校以培育人材
時當末劫。法運垂秋。痛心下淚。何也。佛所囑咐。『波羅提木叉為汝等大師。』又云。『戒如明日月。能消長夜暗。』又曰。『此經能住世。佛法得熾盛。若不持此戒。世界皆暗冥。』今茲佛法衰微。三門塗炭。豈非無因。無奈釋子掛名受戒。而不遵崇。外服袈裟。行同凡俗。是波旬徒屬。作獅子身中虱耳。雲為挽頹風。捐費信施財物。成茲大廈。意欲一一如法。培植人材。常轉法輪。慧命是續。因此建立長期戒壇。逢年傳戒。道不論遠近。人不論多寡。依時而來。傳受戒法。期滿後入學戒堂重行熏習。以資深造。不受寄名。不容簡略。肅戒律也。雲入山十年矣。仗 佛祖威靈。檀越護法。預期十事。次第完成。聊竟憨公未竟之志。今堂宇可容僧伽五百人。租穀亦差足半年糧食。四事供養。具體而微。佛子住持。寧心無慮。敬祈執事。保此道場。雲於此十年間。左支右絀。辛苦撐持。委曲求全。濟變禦侮。其困苦艱難有不堪殫述者。雲今去矣。付與僧徒復仁住持。書此事實。以勵後昆。其或有超世高人。空宗大士。認此為空花佛事。水月道場。雲又何辭。雲嘗恭讀壇經。至五祖以袈裟遮圍。為祖說『金剛經。』至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』祖於言下大悟。即啟五祖言。「何期自性。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。本無生滅。何期自性。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。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。能生萬法。」一路說來。如天花亂墜。前四句何期。是攝用歸體。後一句何期。是全體大用。前四句是自渡。後一句是渡生。能生萬法者。一切種智也。我佛以一大事因緣。出現於世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廣佛法於無邊。渡眾生於無盡。故釋迦不終老於雪山。六祖不永潛於獵隊。為傳佛種智耳。雲雖行能無似。然不敢作最後斷佛種性人。因此數十年來。屢興道場。不惜作童子累土畫沙事。亦本於教亦多術。逗機接引。以傳佛種智耳。安敢作有相無相之論哉。「有情來下種。因地果還生。」願一切有情。同圓種智。
〔編者案〕 師自披緇至今。已九十餘年。不住持現成寺院。不受人家豐腆供養。四眾弟子。前後得戒渡者萬餘人。乞戒歸依者百十萬人。手興大小梵剎數十。其宏麗者如雲南雲棲。其莊嚴者如粵北南華。均費百數十萬銀元。以現值計。幾千萬矣。師以一衲隨身。一笠。一拂。一鏟。一背架。行腳遍海內外。其建築雲棲寺。來也如是。去也如是。其重興南華時。上山也如是。下山也如是。師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蒞粵。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將南華職務付弟子復仁主持。一笠。一拂。一鏟。一背架。一衲隨身。逕往乳源中興雲門寺。此為人人所共見者也。
〔附復仁和尚小傳〕釋復仁。廣東大埔縣人。出家於暹羅甘露寺。具戒於天童。參淨心。果宗。融通。慈舟諸老。禮普陀。五臺。鼓山。住金山高旻。前後八載。有所省發。復依虛雲老和尚於鼓山。重興南華。師奉虛公命。募化於南洋。化緣甚廣。南華得以竟功。至三十一年始返粵。虛公應政府請。往重慶。命師代理住持。嗣繼法脈。傳大戒。至民國三十七年始辭職。獨居大嶼山茅蓬。篤行精勤。師其有焉。(後任交靈源住持又交本煥。)
〔是年大事〕 八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。蔣中正就國府主席。